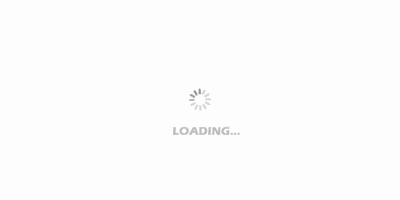艾滋孤兒群體的生存狀況引發關注
昔日的艾滋孤兒代廷梅當爸爸了, 大學畢業后他選擇在智行基金會工作, 救助艾滋孤兒, 回饋社會。 /攝
蔡寺村的衛生站里, 在接受點滴的艾滋病人。 /圖
孤兒楠楠在自已的獎狀前 /圖
南方周末記者 沈穎 發自河南、安徽、北京、天津
寫在前面
2003年8月, 南方周末刊發專題《艾滋遺孤:跟我回家》, 首次披露了河南艾滋孤兒(父母一方或雙方因艾滋病去世, 但本人健康)群體的生存狀況, 引發全國關注,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親赴河南艾滋病村看望病人和孤兒, 此后政府層面“四免一關懷”政策出臺,
Advertisiment
2008年11月30日, 第21個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前夕,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再次探望孤兒們, 幾乎與總理的足跡同路, 南方周末記者時隔5年后再次輾轉河南、天津、安徽、北京四地, 零距離探尋近30名艾滋孤兒已經成年、正在成年、渴望成年的坎坷心路。
當年孩子不少已經長大, 蜷縮著的肩膀似乎已經表面打開, 但傷痕似乎進入更隱秘的內心。 與5年前的懵懂相比, 他們的人生體驗更為深刻, 內心世界亦更復雜, 在嚴酷的客觀環境面前日益呈現嚴重的成長裂變:一部分人經受火一般的歷練而漸入正途, 上大學、讀研、工作, 乃至結婚生子;而另一部分孩子則敗下陣來, 早早輟學, 沒入底層的流浪大軍,
Advertisiment
, 艾滋孤兒的地域分布已遠非媒體早年所披露的僅河南、安徽一隅, 鄰近的山東、湖北、陜西, 甚至青海、內蒙、新疆等邊遠省份亦有蹤跡, 正從一個局部高發現象, 變成一個全國性問題, 某些地區仍處于信息不公開狀態, 影響了孤兒救助的及早有效進行。
更為重要的是, 5年過去了, 既往救助艾滋孤兒的路徑也亟需全面審視, 檢討得失, 正如待剝的洋蔥, 從低層次的生存需要的滿足到進一步的教育問題的被重視, 再至更內在的情感救濟、心理危機干預, 亟待國家和全社會的對癥解難, 每一個生命的成長, 緊要處就這么幾步,
Advertisiment
注:“四免一關懷”, 即免費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免費咨詢檢測艾滋病病毒抗體、免費提供母嬰阻斷藥物和嬰兒檢測試劑、為艾滋病遺孤提供免費義務教育, 將經濟困難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屬, 納入政府補助范圍。
蔡寺村的257名孤兒
如今9人已經成為大學生, 24人就讀于高中或技校, 而更多已成年的孩子早早輟學去沿海發達地區打工, 有人出外打工十年從來沒回過家鄉。
2008年11月29日下午6點, 安徽省阜陽市阜南縣王化鎮蔡寺村防疫站門口, 從北京專程趕來的溫家寶總理和十個艾滋孤兒——握手。 17歲的高二學生陳建飛是最大的一個孩子。
“你們的學費和生活費怎么解決?”溫家寶問。
“香港智行基金會給我提供全部學費,
Advertisiment
溫家寶回頭囑咐陪同的安徽省及阜南縣官員說, “救助艾滋孤兒, 國家雖然投入了不少, 但做得還不夠, 民間慈善機構緩解了政府的困難, 起了補充作用。 ”
巧合的是, 就在溫總理所站的空地上, 兩天前上午, 智行基金會安徽辦公室工作人員馬正洲忙著第5次給該村二百余個艾滋孤兒集中發放學費和生活補助。
蔡寺村, 與河南交界, 艾滋病魔自上世紀90年代借中原賣血風潮蔓延至此, 整個村莊從此陰霾不散。 這是阜陽市艾滋病疫情最高發的村莊, 艾滋孤兒也最集中, 救助工作沉重, 這也許是溫總理選擇造訪的原因。
截至目前, 據阜南縣疾控中心統計, 蔡寺村共有在冊艾滋病人115人。
Advertisiment
已經連續十年致力于艾滋孤兒救助的香港智行基金會在蔡寺村資助上學的孩子總計257人。 如今9人已經成為大學生, 24人就讀于高中或技校, 即將步入社會。
從2006年8月至今, 馬正洲記不清多少次騎著摩托車卷著塵土到這個村子, 彼時, 他被看作“騙子”, 現在則被視為“家人”。
更多的孩子仍在成長的路上艱辛邁步。 總理造訪前的一周, 腰莊、后宅、程寨村組走訪中觀察到, 一人或多人感染艾滋的家庭, 景況窘迫, 政府派送的電視機是唯一醒目的家什。
這些家庭一般有2至3個孩子, 多的達五六個, 以父母中一方去世的單孤居多, 雙孤較少。正值周末,上學的孩子就擠在逼仄的屋內小板凳上做功課,“下雨時屋子里都是濕的”,一個孩子指著破了一個大洞的屋頂說。
迫于生計和照顧孩子,村里新出現了艾滋病人組合家庭,一對感染夫妻,丈夫去世,仍存活的妻子與另一個失去妻子的男感染者重新組合成家庭,他們的孩子貌似脫去了孤兒的身份,但處境依然。
而更多已成年的孩子早早輟學去沿海發達地區打工,除非主動打村上電話回來,沒人知道他們在哪里出沒,過得如何,“有人出外打工十年從來沒回過家鄉,反正父母不在了”。
在縣城,溫家寶再度見到了兩年前到中南海做客的孤兒楠楠,并欣然在送給她的字典上題字,“要站立起來,自己走路,不用拐杖”。然而,現實是,對于太多的孤兒而言,扔掉拐杖,何其之難。
20%的受助輟學率驚人
“8年前,只要我愿意給錢,他們都盼著讀書,現在我愿意給錢,他們似乎不愿意讀了。 ”
和溫總理握手的陳建飛如今在讀高二,立志考大學。
兩年前,15歲的他已受到智行基金會的資助上學,按照資助規則,先行繳納學費再事后報銷。但先期周轉的1000元學費難倒了他,已成家的姐姐電話過來要斷絕關系,奶奶不僅要將智行資助的部分學費占為己用,還跟他算賬歸還以前的開支。各自窘困的家境使得親情出奇淡漠,一度逼迫小建飛動了放棄學業的念頭。后來智行基金會為他改了規矩直接給錢,窘迫才緩解,他的人生也得以越過第一個十字路口。
兩年來,蔡寺村給馬正洲最深的印象是,“輟學的孩子太多了。”他說,在目前救助的孩子中,別說考上大學的鳳毛麟角,堅持讀高中的已屬罕見,不少艾滋孤兒早早輟學打工,有的在小學就終止了學業,“二百多個孩子,少數是被反復勸回來讀書的,更多的拽也拽不住。”
兩年前,16歲的孫莉莉就因為“家里連油都吃不起才出去打工”。她謊報年齡在南方一皮包廠里干了一年多,“早上7點到晚上12點多,至少做600個包,完不成任務要罰款。”后來智行基金會的人找到她,資助她繼續讀書,她不敢相信,“笑了一整天,忘了吃飯,我以為自己一輩子就這么渾渾噩噩地過去了”。
輟學現象絕非蔡寺村獨有。11月初,智行基金會的負責人杜聰在鄭州跟幾十個大學生聚會,這些孩子都曾經是艾滋孤兒。他做了個即興調查,在43個大學生中,本人曾經有過輟學念頭的有28個,而其中34個大學生的兄弟姐妹中至少一人未讀完初中就已輟學外出打工。
杜聰在河南已做了8年艾滋孤兒救助,他說:“8年前,只要我愿意給錢,他們都想盼著讀書,現在我愿意給錢,他們似乎不愿意讀了。”
這“不只是資金缺乏”那么簡單。
杜聰認為,農村的價值觀的改變令艾滋家庭的觀念首當其沖受到沖擊,“讀書經濟回報低周期長”、“看見別人打工回來穿金戴銀的誘惑”等內在因素日趨影響了家長和孩子的人生選擇。
輟學打工的孤兒們大多隱于人海,音訊全無,智行基金會資助的數據中,因輟學而使資助中斷的例子逐年增多,估計在20%左右。個別被智行成功勸回學校的孤兒的外出遭遇預示著打工之途并不平坦。
2008年5月,萬光輝從浙江平湖一家“黑工廠”逃回了家。他在流水線上做了3個月的服裝,卻沒拿到一分錢,想離開,保安日夜看守不準走,他偷偷給馬正洲打電話求救,馬報了警,才脫了險。
暴力傾向與歧路可能
“他根深蒂固地認為從小受到的嘲笑、不公的命運和仇恨只有通過暴力發泄才舒服一些。 ”
“人很多,溫總理卻站在靠我們最近的地方,我們圍著他”,陳建飛說,身邊的孩子們不敢相信總理真的來了,緊張得不敢說話。陳建飛覺得自己比過去開朗多了,他發現自己是唯一一個敢當眾回答總理問題的孩子。
停留半個多小時后,總理一行繼續趕赴醫院看望艾滋病人。陳建飛還有許多發自內心的話來不及對總理說。
他想說,如果不是社會的關懷,讓他釋放了心里的仇恨,“也許我就走上歧路了”。他還想說,很多孩子并不這么幸運。
現在的陳建飛痛心于幾個同村孤兒日漸嚴重的暴力傾向,“他們有的既不上學,也不去打工,四處游蕩,撬門打游戲,在學校充當小打手收取保護費。”
陳建飛目睹著從小一起長大的小學同學王強在父母去世后,性格日變,最后發展到去賭場充當打手,在一次打架斗毆中被抓,被判了5年。“他崇拜暴力,仗著自己是艾滋孤兒,誰也不敢惹,大人也敢打。”
出事前兩個月,陳建飛找到王強,想規勸他放棄暴力,深談后他發現自己已經無力改變他的看法,“他根深蒂固地認為從小受到的嘲笑、不公的命運和仇恨只有通過暴力發泄才舒服一些”。
11月23日下午,蔡寺村后宅,間僅3米長2米寬的破土屋,沒水沒電,這就是打工逃回的萬光輝的家,他和哥哥在父母艾滋病死后一直在此蝸居。“我不愿意再回到這間屋子,”萬光輝說,這里灌滿了悲傷的記憶。去年12月,19歲的哥哥萬光榮因輪☆禁☆奸罪被抓,現在合肥某處監獄服刑,判了12年。
屋內桌上,異常醒目的是一個觀音像。“過年的時候每天必擦,擦得發亮”。哥哥在外打工后,也常告訴他一個人呆著別害怕,“有觀音保佑”。
哥哥在弟弟眼里“很顧家”,父親死后,讀四年級的哥哥輟學打工供弟弟上學,要照顧弟弟,他不敢走遠,就近到縣城建筑工地幫人搬磚頭打雜。15歲時出遠門,間隔一段時間從外地打村里電話,叮囑弟弟好好讀書,寄回錢來給他交學費。
兩年前,弟弟發現哥哥變了,在外面交了不三不四的朋友回來,染著黃頭發,喝酒,走路嘴里叼著煙。最后他把自己送入監獄。
掉進犯罪黑洞的孩子不只是安徽孤案。河南大學生張勝利和在北京當保安的弟弟已經失去聯系快2個月了。兄弟倆同受社會資助,卻已然有了永不交叉的異樣人生。兩年前,幾個小混混拉著他弟弟去一個修理廠偷一萬多塊錢,“錢是他們拿的,我弟弟負責給他們望風。”出事后,小混混的家人花錢打點關系,把自己兒子保出來,“只有我弟弟被抓去判了刑”。
難以愈合的心理創傷
“最近沒有開心的事”,“沒人愿意和我玩”,“當別人喊爸爸媽媽時,我很難受”,“沒有什么事能讓我感覺好些”,“我覺得沒有人能幫我”。
陳建飛覺得判了刑的王強并不是天生壞人,“如果早點有人跟他聊聊,打開心結,不至于掉進深淵”,“他心里壓抑得太久了,無法承受”。陳建飛認為,暴力傾向的內在癥結是心里淤積的痛苦經驗得不到釋放。
智行基金會的馬正洲接觸的艾滋孤兒中心理問題最嚴重的是17歲的劉云飛。在基金會為孤兒們舉辦的夏令營里,有個工作人員看了他一眼,他就很難受,找馬正洲,問“是不是他瞧不起我,因為我是孤兒”。他甚至只因一個小細節就與工作人員打起來,以為別人要欺負他。馬正洲一找他談話,他就跪在那里說知道自己錯了。
11月21日,劉云飛所在的技校給馬正洲打緊急電話,說劉云飛因為在寢室丟了一雙新球鞋,指責學校的安全工作太差,鬧著不上學了,“沖動起來還流露出輕生念頭”。
七十多歲的爺爺從農村趕來買了雙新鞋給他,“鞋子是小事。”劉云飛說。
入談心,劉云飛沉默很久才說出心里的掙扎,永遠忘不了小時候失去父母后,同學欺負他,罵他“艾滋病家里來的,有娘養沒娘教”。他受了刺激,以后就變得極其敏感脆弱,“老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沖動過后又很后悔”。
跟老師發生沖突后,劉云飛當時道了歉,第二天又“感覺心里煩”,在宿舍抽煙,被老師發現沒收了煙。他盯著老師要,又發生沖突,差點打起來,后來干脆翻墻跑了失蹤了。馬正洲只好報案讓警察找,所幸第二天他自己回來了。“當時我很煩,想找個安靜的地方躲起來,就去了旅店住了一宿。”劉云飛說。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高燕寧教授和碩士生丁中華曾采用專業心理學量表,根據智行助學名單,評定了120名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狀況,對雙孤、單親和雙親家庭的孩子進行比較分析。
結果表明,雙孤家庭的孩子相對于單親和雙親家庭的孩子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心理問題,包括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恐怖、偏執、精神病性等癥狀。高燕寧不無擔憂,這些調查的孩子都受到了智行的助學,日常接受了較多的社會支持,心理隱患尚如此,而那些未接受助學的孩子呢?
智行基金會曾在艾滋病高發村的3所學校和一所孤兒院隨機選取了25個艾滋孤兒進行深入心理訪談,結果大多數孩子回答“最近沒有開心的事”,“沒人愿意和我玩”,“當別人喊爸爸媽媽時,我很難受”。有煩惱時,許多孩子選擇“不告訴任何人,沒有什么事能讓我感覺好些”,“我覺得沒有人能幫我”。
心理的創傷隱秘而沉重。在造訪艾滋病家庭前,杜聰從來沒有失眠的問題,但這些年來他不只失眠,還常常做噩夢,有時半夜醒來無故哭泣。杜聰由己推及那些孤兒,他曾遇到過一個女孩,一家3代8口人,只有她一個是健康的,其余7個都有艾滋病,“你能想象年幼的她眼睜睜的看著一個個親人離開,怎么渡過心理危機?”
受智行資助上學的孤兒,每年都會寫信給基金會報告這一年的經歷和感受,八年未有間斷,智行基金會的負責信件整理工作的阿東這半年來憂慮重重,早年被發現的艾滋家庭,病毒多年潛伏后正日漸發作,不少單孤的孩子將不可遏止地面對僅有的親人死亡,從而墮入雙孤境地,心理疾患也許會越來越糟。
一個已經讀了大學的孤兒說,每次跟患病的媽媽通電話,說出來的都是安慰的話語,每次總有一段尷尬的沉默,在那段空白里她總是意識到,她和媽媽都在隱藏自己真實的想法,誰都知道說的是謊言,誰都不想先拆除它,這令她郁悶不已。
苦難,就像充電
“艾滋孤兒也能成功,和其他人一樣,沒什么不同,也上大學,也有所成就。 ”
5年前本報報道的高燕現在上大學了,在衛生學院讀書,她比過去開朗些了,能主動跟人說話了,但很難和人交心,磨難的經歷使她總是處于過度自我保護之中,對孤兒身份極為敏感。總是不得已隱瞞和編織一些信息,她習慣了跟班里同學主動強調,她爸爸媽媽在縣里工作,說來看她的人都是爸媽的好朋友。
在智行資助的8000名艾滋孤兒中,有300個已經考上了大學,他們是艾滋孤兒中最優秀的一群。與同齡人相比,他們更內向,沉默,心思細密,眼神里有不經意的憂郁,但性格也更剛毅,有耐力,執著。
去年,張勝利以630多的高分考入北京一所重點大學的計算機專業,今年以其踏實肯干被選為班長,盡管“開始時當眾說話都聲音顫抖”。
求學路的艱難源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我媽有精神病。”從3歲起,張勝利就生活在噩夢中,“媽媽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家,病發時總是離家出走,我爸就去找,找之前先算一卦,朝哪個方向跑了,就去那個方向找。十多年里,我爸找我媽所跑的路,可以把河南省繞幾圈。十年前,最后一次終于找不著了,我也沒再見過我媽。”
母親失蹤3年后,父親陷入艾滋病泥潭。那年,16歲的張勝利讀初三,住校,交不起20元的住宿費,學校給免了,老師說“你從家里帶床被子來就行”,張勝利無比難堪,“家里就一床破被子,沒有多余的”。
從高中起,他開始接受智行基金會的資助,學費有了著落,生活境況也好轉。極端的貧窮、“沒媽的孩子”的嘲笑、父親艾滋病陰影的糾纏,反過來磨煉了張勝利驚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學習倦了,每次回家都像是快速充電,刺激了我向上的心志。”
大一新生劉一凡也受到父親的激勵,父親是艾滋高發村里第一個服藥后挺過來的病人,“躺在床上半個多月,快準備后事了,我爸爸苦撐著,能走幾步路了,他在前面走,村里人在后面鼓掌。”父親重新站起來給了其他病人希望,病好點他就看養殖書,買回飼料,自己養牛掙錢。“他的勇氣影響了我,我為他驕傲。”劉一凡說。
學電子技術的研究生張健,在就業形勢極其惡劣的寒冬,通過層層嚴酷考核,最近被一家全國知名的取,提前找到了工作。7年前,父親查出艾滋病,“當時的感覺是崩潰”。村里的規矩是考上大學后要在村里放映兩場電影,身患艾滋的父親無力付錢,他由此許了一個承諾,替爸爸還愿。2006年保送研究生后,他自己攢夠了錢,在村里放了一場電影,是喜劇片,那時父親去世兩年,“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見到了我爸,他很高興,但對我說,你許的愿是兩場,怎么只放了一場?”
劉一凡考上大學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兩個夢想,第一個是在家鄉建一個紀念碑,“紀念這場艾滋病災難”,第二個夢想是,“將來當村官,讓家鄉像華西村一樣富裕。首要的是建設一些工廠,讓那么多艾滋病人可以邊服藥邊干點力所能及的活掙點錢。”他痛心于“父輩帶病在外打工,中途不斷回家來拿藥”的悲戚。
汶川大地震后,智行基金會資助了一些成年的艾滋孤兒去災區給地震孤兒上課,這讓劉一凡重拾了自尊和自信,他說,這是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有能力幫助別人,“那種感覺真好,我不再覺得自己是社會的負擔”。
張健內心極其渴望“成功”。他知道,如果他能成功,對其他更小的艾滋孤兒是個積極影響,也能影響別人的看法,“艾滋孤兒也能成功,和其他人一樣,沒什么不同,也上大學,也有所成就”。
智行基金會目前的工作人員中有6個是曾受資助的艾滋孤兒。其中之一安徽辦公室的代廷梅可能是最早結婚并當爸爸的。
他也想大學畢業后多掙錢養家,但是他知道有更多的孤兒處在比他更惡劣的艾滋陰影中,“如果我是沒有鞋子的那個,他們是沒有腳的人”。
為了這些“沒有腳”的人,代廷梅說要在智行至少堅持干十年,跑村家訪很辛苦收入不高,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如同在火場救火,“如果等自己掙夠了錢再回來救人,孩子們可能早被火吞了,時間不等人”。
哪里有愛,哪里就有光
“他就像個小天使,他的生命注定會很短暫,但他生命的價值也許不僅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喚醒別人。 雙孤較少。正值周末,上學的孩子就擠在逼仄的屋內小板凳上做功課,“下雨時屋子里都是濕的”,一個孩子指著破了一個大洞的屋頂說。
迫于生計和照顧孩子,村里新出現了艾滋病人組合家庭,一對感染夫妻,丈夫去世,仍存活的妻子與另一個失去妻子的男感染者重新組合成家庭,他們的孩子貌似脫去了孤兒的身份,但處境依然。
而更多已成年的孩子早早輟學去沿海發達地區打工,除非主動打村上電話回來,沒人知道他們在哪里出沒,過得如何,“有人出外打工十年從來沒回過家鄉,反正父母不在了”。
在縣城,溫家寶再度見到了兩年前到中南海做客的孤兒楠楠,并欣然在送給她的字典上題字,“要站立起來,自己走路,不用拐杖”。然而,現實是,對于太多的孤兒而言,扔掉拐杖,何其之難。
20%的受助輟學率驚人
“8年前,只要我愿意給錢,他們都盼著讀書,現在我愿意給錢,他們似乎不愿意讀了。 ”
和溫總理握手的陳建飛如今在讀高二,立志考大學。
兩年前,15歲的他已受到智行基金會的資助上學,按照資助規則,先行繳納學費再事后報銷。但先期周轉的1000元學費難倒了他,已成家的姐姐電話過來要斷絕關系,奶奶不僅要將智行資助的部分學費占為己用,還跟他算賬歸還以前的開支。各自窘困的家境使得親情出奇淡漠,一度逼迫小建飛動了放棄學業的念頭。后來智行基金會為他改了規矩直接給錢,窘迫才緩解,他的人生也得以越過第一個十字路口。
兩年來,蔡寺村給馬正洲最深的印象是,“輟學的孩子太多了。”他說,在目前救助的孩子中,別說考上大學的鳳毛麟角,堅持讀高中的已屬罕見,不少艾滋孤兒早早輟學打工,有的在小學就終止了學業,“二百多個孩子,少數是被反復勸回來讀書的,更多的拽也拽不住。”
兩年前,16歲的孫莉莉就因為“家里連油都吃不起才出去打工”。她謊報年齡在南方一皮包廠里干了一年多,“早上7點到晚上12點多,至少做600個包,完不成任務要罰款。”后來智行基金會的人找到她,資助她繼續讀書,她不敢相信,“笑了一整天,忘了吃飯,我以為自己一輩子就這么渾渾噩噩地過去了”。
輟學現象絕非蔡寺村獨有。11月初,智行基金會的負責人杜聰在鄭州跟幾十個大學生聚會,這些孩子都曾經是艾滋孤兒。他做了個即興調查,在43個大學生中,本人曾經有過輟學念頭的有28個,而其中34個大學生的兄弟姐妹中至少一人未讀完初中就已輟學外出打工。
杜聰在河南已做了8年艾滋孤兒救助,他說:“8年前,只要我愿意給錢,他們都想盼著讀書,現在我愿意給錢,他們似乎不愿意讀了。”
這“不只是資金缺乏”那么簡單。
杜聰認為,農村的價值觀的改變令艾滋家庭的觀念首當其沖受到沖擊,“讀書經濟回報低周期長”、“看見別人打工回來穿金戴銀的誘惑”等內在因素日趨影響了家長和孩子的人生選擇。
輟學打工的孤兒們大多隱于人海,音訊全無,智行基金會資助的數據中,因輟學而使資助中斷的例子逐年增多,估計在20%左右。個別被智行成功勸回學校的孤兒的外出遭遇預示著打工之途并不平坦。
2008年5月,萬光輝從浙江平湖一家“黑工廠”逃回了家。他在流水線上做了3個月的服裝,卻沒拿到一分錢,想離開,保安日夜看守不準走,他偷偷給馬正洲打電話求救,馬報了警,才脫了險。
暴力傾向與歧路可能
“他根深蒂固地認為從小受到的嘲笑、不公的命運和仇恨只有通過暴力發泄才舒服一些。 ”
“人很多,溫總理卻站在靠我們最近的地方,我們圍著他”,陳建飛說,身邊的孩子們不敢相信總理真的來了,緊張得不敢說話。陳建飛覺得自己比過去開朗多了,他發現自己是唯一一個敢當眾回答總理問題的孩子。
停留半個多小時后,總理一行繼續趕赴醫院看望艾滋病人。陳建飛還有許多發自內心的話來不及對總理說。
他想說,如果不是社會的關懷,讓他釋放了心里的仇恨,“也許我就走上歧路了”。他還想說,很多孩子并不這么幸運。
現在的陳建飛痛心于幾個同村孤兒日漸嚴重的暴力傾向,“他們有的既不上學,也不去打工,四處游蕩,撬門打游戲,在學校充當小打手收取保護費。”
陳建飛目睹著從小一起長大的小學同學王強在父母去世后,性格日變,最后發展到去賭場充當打手,在一次打架斗毆中被抓,被判了5年。“他崇拜暴力,仗著自己是艾滋孤兒,誰也不敢惹,大人也敢打。”
出事前兩個月,陳建飛找到王強,想規勸他放棄暴力,深談后他發現自己已經無力改變他的看法,“他根深蒂固地認為從小受到的嘲笑、不公的命運和仇恨只有通過暴力發泄才舒服一些”。
11月23日下午,蔡寺村后宅,間僅3米長2米寬的破土屋,沒水沒電,這就是打工逃回的萬光輝的家,他和哥哥在父母艾滋病死后一直在此蝸居。“我不愿意再回到這間屋子,”萬光輝說,這里灌滿了悲傷的記憶。去年12月,19歲的哥哥萬光榮因輪☆禁☆奸罪被抓,現在合肥某處監獄服刑,判了12年。
屋內桌上,異常醒目的是一個觀音像。“過年的時候每天必擦,擦得發亮”。哥哥在外打工后,也常告訴他一個人呆著別害怕,“有觀音保佑”。
哥哥在弟弟眼里“很顧家”,父親死后,讀四年級的哥哥輟學打工供弟弟上學,要照顧弟弟,他不敢走遠,就近到縣城建筑工地幫人搬磚頭打雜。15歲時出遠門,間隔一段時間從外地打村里電話,叮囑弟弟好好讀書,寄回錢來給他交學費。
兩年前,弟弟發現哥哥變了,在外面交了不三不四的朋友回來,染著黃頭發,喝酒,走路嘴里叼著煙。最后他把自己送入監獄。
掉進犯罪黑洞的孩子不只是安徽孤案。河南大學生張勝利和在北京當保安的弟弟已經失去聯系快2個月了。兄弟倆同受社會資助,卻已然有了永不交叉的異樣人生。兩年前,幾個小混混拉著他弟弟去一個修理廠偷一萬多塊錢,“錢是他們拿的,我弟弟負責給他們望風。”出事后,小混混的家人花錢打點關系,把自己兒子保出來,“只有我弟弟被抓去判了刑”。
難以愈合的心理創傷
“最近沒有開心的事”,“沒人愿意和我玩”,“當別人喊爸爸媽媽時,我很難受”,“沒有什么事能讓我感覺好些”,“我覺得沒有人能幫我”。
陳建飛覺得判了刑的王強并不是天生壞人,“如果早點有人跟他聊聊,打開心結,不至于掉進深淵”,“他心里壓抑得太久了,無法承受”。陳建飛認為,暴力傾向的內在癥結是心里淤積的痛苦經驗得不到釋放。
智行基金會的馬正洲接觸的艾滋孤兒中心理問題最嚴重的是17歲的劉云飛。在基金會為孤兒們舉辦的夏令營里,有個工作人員看了他一眼,他就很難受,找馬正洲,問“是不是他瞧不起我,因為我是孤兒”。他甚至只因一個小細節就與工作人員打起來,以為別人要欺負他。馬正洲一找他談話,他就跪在那里說知道自己錯了。
11月21日,劉云飛所在的技校給馬正洲打緊急電話,說劉云飛因為在寢室丟了一雙新球鞋,指責學校的安全工作太差,鬧著不上學了,“沖動起來還流露出輕生念頭”。
七十多歲的爺爺從農村趕來買了雙新鞋給他,“鞋子是小事。”劉云飛說。
入談心,劉云飛沉默很久才說出心里的掙扎,永遠忘不了小時候失去父母后,同學欺負他,罵他“艾滋病家里來的,有娘養沒娘教”。他受了刺激,以后就變得極其敏感脆弱,“老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沖動過后又很后悔”。
跟老師發生沖突后,劉云飛當時道了歉,第二天又“感覺心里煩”,在宿舍抽煙,被老師發現沒收了煙。他盯著老師要,又發生沖突,差點打起來,后來干脆翻墻跑了失蹤了。馬正洲只好報案讓警察找,所幸第二天他自己回來了。“當時我很煩,想找個安靜的地方躲起來,就去了旅店住了一宿。”劉云飛說。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高燕寧教授和碩士生丁中華曾采用專業心理學量表,根據智行助學名單,評定了120名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狀況,對雙孤、單親和雙親家庭的孩子進行比較分析。
結果表明,雙孤家庭的孩子相對于單親和雙親家庭的孩子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心理問題,包括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恐怖、偏執、精神病性等癥狀。高燕寧不無擔憂,這些調查的孩子都受到了智行的助學,日常接受了較多的社會支持,心理隱患尚如此,而那些未接受助學的孩子呢?
智行基金會曾在艾滋病高發村的3所學校和一所孤兒院隨機選取了25個艾滋孤兒進行深入心理訪談,結果大多數孩子回答“最近沒有開心的事”,“沒人愿意和我玩”,“當別人喊爸爸媽媽時,我很難受”。有煩惱時,許多孩子選擇“不告訴任何人,沒有什么事能讓我感覺好些”,“我覺得沒有人能幫我”。
心理的創傷隱秘而沉重。在造訪艾滋病家庭前,杜聰從來沒有失眠的問題,但這些年來他不只失眠,還常常做噩夢,有時半夜醒來無故哭泣。杜聰由己推及那些孤兒,他曾遇到過一個女孩,一家3代8口人,只有她一個是健康的,其余7個都有艾滋病,“你能想象年幼的她眼睜睜的看著一個個親人離開,怎么渡過心理危機?”
受智行資助上學的孤兒,每年都會寫信給基金會報告這一年的經歷和感受,八年未有間斷,智行基金會的負責信件整理工作的阿東這半年來憂慮重重,早年被發現的艾滋家庭,病毒多年潛伏后正日漸發作,不少單孤的孩子將不可遏止地面對僅有的親人死亡,從而墮入雙孤境地,心理疾患也許會越來越糟。
一個已經讀了大學的孤兒說,每次跟患病的媽媽通電話,說出來的都是安慰的話語,每次總有一段尷尬的沉默,在那段空白里她總是意識到,她和媽媽都在隱藏自己真實的想法,誰都知道說的是謊言,誰都不想先拆除它,這令她郁悶不已。
苦難,就像充電
“艾滋孤兒也能成功,和其他人一樣,沒什么不同,也上大學,也有所成就。 ”
5年前本報報道的高燕現在上大學了,在衛生學院讀書,她比過去開朗些了,能主動跟人說話了,但很難和人交心,磨難的經歷使她總是處于過度自我保護之中,對孤兒身份極為敏感。總是不得已隱瞞和編織一些信息,她習慣了跟班里同學主動強調,她爸爸媽媽在縣里工作,說來看她的人都是爸媽的好朋友。
在智行資助的8000名艾滋孤兒中,有300個已經考上了大學,他們是艾滋孤兒中最優秀的一群。與同齡人相比,他們更內向,沉默,心思細密,眼神里有不經意的憂郁,但性格也更剛毅,有耐力,執著。
去年,張勝利以630多的高分考入北京一所重點大學的計算機專業,今年以其踏實肯干被選為班長,盡管“開始時當眾說話都聲音顫抖”。
求學路的艱難源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我媽有精神病。”從3歲起,張勝利就生活在噩夢中,“媽媽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家,病發時總是離家出走,我爸就去找,找之前先算一卦,朝哪個方向跑了,就去那個方向找。十多年里,我爸找我媽所跑的路,可以把河南省繞幾圈。十年前,最后一次終于找不著了,我也沒再見過我媽。”
母親失蹤3年后,父親陷入艾滋病泥潭。那年,16歲的張勝利讀初三,住校,交不起20元的住宿費,學校給免了,老師說“你從家里帶床被子來就行”,張勝利無比難堪,“家里就一床破被子,沒有多余的”。
從高中起,他開始接受智行基金會的資助,學費有了著落,生活境況也好轉。極端的貧窮、“沒媽的孩子”的嘲笑、父親艾滋病陰影的糾纏,反過來磨煉了張勝利驚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學習倦了,每次回家都像是快速充電,刺激了我向上的心志。”
大一新生劉一凡也受到父親的激勵,父親是艾滋高發村里第一個服藥后挺過來的病人,“躺在床上半個多月,快準備后事了,我爸爸苦撐著,能走幾步路了,他在前面走,村里人在后面鼓掌。”父親重新站起來給了其他病人希望,病好點他就看養殖書,買回飼料,自己養牛掙錢。“他的勇氣影響了我,我為他驕傲。”劉一凡說。
學電子技術的研究生張健,在就業形勢極其惡劣的寒冬,通過層層嚴酷考核,最近被一家全國知名的取,提前找到了工作。7年前,父親查出艾滋病,“當時的感覺是崩潰”。村里的規矩是考上大學后要在村里放映兩場電影,身患艾滋的父親無力付錢,他由此許了一個承諾,替爸爸還愿。2006年保送研究生后,他自己攢夠了錢,在村里放了一場電影,是喜劇片,那時父親去世兩年,“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見到了我爸,他很高興,但對我說,你許的愿是兩場,怎么只放了一場?”
劉一凡考上大學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兩個夢想,第一個是在家鄉建一個紀念碑,“紀念這場艾滋病災難”,第二個夢想是,“將來當村官,讓家鄉像華西村一樣富裕。首要的是建設一些工廠,讓那么多艾滋病人可以邊服藥邊干點力所能及的活掙點錢。”他痛心于“父輩帶病在外打工,中途不斷回家來拿藥”的悲戚。
汶川大地震后,智行基金會資助了一些成年的艾滋孤兒去災區給地震孤兒上課,這讓劉一凡重拾了自尊和自信,他說,這是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有能力幫助別人,“那種感覺真好,我不再覺得自己是社會的負擔”。
張健內心極其渴望“成功”。他知道,如果他能成功,對其他更小的艾滋孤兒是個積極影響,也能影響別人的看法,“艾滋孤兒也能成功,和其他人一樣,沒什么不同,也上大學,也有所成就”。
智行基金會目前的工作人員中有6個是曾受資助的艾滋孤兒。其中之一安徽辦公室的代廷梅可能是最早結婚并當爸爸的。
他也想大學畢業后多掙錢養家,但是他知道有更多的孤兒處在比他更惡劣的艾滋陰影中,“如果我是沒有鞋子的那個,他們是沒有腳的人”。
為了這些“沒有腳”的人,代廷梅說要在智行至少堅持干十年,跑村家訪很辛苦收入不高,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如同在火場救火,“如果等自己掙夠了錢再回來救人,孩子們可能早被火吞了,時間不等人”。
哪里有愛,哪里就有光
“他就像個小天使,他的生命注定會很短暫,但他生命的價值也許不僅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喚醒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