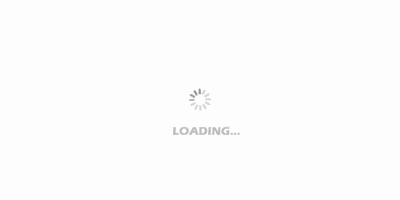從幼稚園開始到小學三年級, 我都是家長和老師眼中的學霸。 分數從來沒有下降到第三名, 甚至有一個學期, 每一科目每一次測試, 都是第一名, 導致全年級老師圍在一起改我的卷子, 一起感慨:“啊, 又是第一名啊!”
小時候, 讀書優秀的孩子自然就有很多“優待”, 比如班幹部, 或者各種社團的組織領導崗位, 所以我一直都在班裡擔任班長等各種“虛職”。
Advertisiment
到了小學四年級, 整個學校進行分班重組, 原來熟悉的一到三年級重新打散, 一群陌生的孩子們組成了一個新班級。 雖然不知道學校為什麼這麼做, 但是在這群新班級裡, 我之前認識的同學, 還不到5%。
因為學習成績一直排優, 所以還是擔任班長, 老師給我組了一個班幹部團隊, 從副班長到體育委員等一個班幹部組織。
自這個新班級開始後, 我的這一年的學涯生活, 開始走向了我始料不及的方向。
被人霸淩的感覺是怎麼樣的?我其實現在想起來也不大記得了。
不只是孩子們之間的遊戲。 因為並不是在一個遊戲裡彼此推推擋擋, 然後嘻嘻鬧鬧散去。 我被推擠過、抓過頭髮、踢過、頭被扔過東西、被推進泥坑裡、被人圍觀髒兮兮的我並被哄堂大笑……
Advertisiment
不只是孩子們之間的玩笑。 因為並不只是說一些幽默的話, 俏皮的故事, 大家聊天調節一下環境和氣氛。 我被取過各種外號, 只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的就被哄笑, 又被威脅過要在一個地方站上兩小時, 否則就會被“關禁閉”, 我的舞蹈姿勢一直被戲謔為“畸形”……
不只是孩子們之間的小圈子。 我基本上沒有朋友, 之前的朋友因為害怕“連帶關係”, 被強勢的人威脅不可以靠近我, 我曾經的好閨密也不願意再和我說話, 每次體育課我都是被隔離在最後一個位置, 沒有人和我搭檔, 就好像我是完全不受歡迎的人。
我一直至今都會做夢夢到一個空蕩蕩的操場, 是的, 這個夢我可能會記一輩子。 我抬頭看著陽光,
Advertisiment
那不僅僅是一個夢境, 往事因為深深印刻在我的記憶裡, 最終被留存在夢中反復播放, 成為長期甚至終生記憶。
長達一年。
我被霸淩的日子持續了整個學年。 我覺得我的四年級是一直處在一種“完全分裂”的狀態。
我身邊的所有老師, 都沒有把這件事情當成一回事。 霸淩的孩子們, 在和被霸淩的我相處過程中, 面對老師時和我極其親密, 牽手、抱腰、搭肩, 大家笑得極其天真和爛漫, 但這樣子的目光在我心中卻是戰戰兢兢的。
霸淩的發起人是副班長,
Advertisiment
慶倖的是, 我的成績在霸淩的一年裡, 一如既往的第一名, 我的體育課和其他才藝課的表現, 也同樣是一如既往的第一名, 我在老師面前始終是聽話、乖巧、安分的孩子, 從沒有什麼不妥當的表現。
我身邊的父母和祖輩, 也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隱藏不說, 一是害怕和恐懼, 二是我覺得“我不應該讓大家擔心”。 當年家裡遇到一些困難, 母親患病, 父親扛下一個家, 所以我主要和年邁的爺爺奶奶一起住。 我自己也努力“催眠”自己,
Advertisiment
可是, 我每天晚上都躲在被子裡偷偷地哭呢。 夜深人靜的時候, 沒有作業, 沒有其他的事情的分心, 只有自我和當天發生的記憶。 我身體被霸淩的經歷, 和我的記憶嘗試催眠自己的部分, 是完全衝突的, 我接受不了, 導致最直接的反應就是我的情緒在夜晚開始瓦解, 開始哭泣。
但是第二天起床, 我又給自己打氣, 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我可以再試試看。
我逐漸發現, 想要試圖讓霸淩者接受我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我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大家都很害怕霸淩者,因為她儼然把握了班裡的所有話語權,所以我和其他朋友的相處,是看著霸淩者的眼色來定相處程度的。霸淩者主動親近我了,大家就和我玩,霸淩者開始欺負我了,大家就遠離我。
我開始逐漸發現,我變得越來越不像我,變成一個越來越讓我厭惡的自己。
要融入到霸淩者的圈子,要先學會賄賂,我得先偷偷地把自己的壓歲錢從奶奶贈給我的小豬儲錢罐裡拿出來。錢越來越少,爺爺發現了,那天他來問我:“是學校裡要交什麼費麼,怎麼感覺壓歲錢都快沒了?”,那次對話我一輩子也忘記不了,我耷拉著點頭說,“是的,是的”。
要融入到霸淩者的圈子,要先學會跟隨,丟掉自己的主見,唯唯諾諾,唯霸淩者的話是真理,我開始晚出晚歸,因為我要幫霸淩者做完作業,替她籌備好明天上學的東西,我才能夠回家。
我從小都是一個乖巧、愛學習、全部人眼中可愛、聰明又優秀的孩子,但是我將自己珍惜的壓歲錢,將自己珍貴的品質,卻拿來作為賄賂的籌碼,換來別人假假真真的“接受”。
當我終於接受不了,放棄這種做法的時候,不出意外,我遭受到了更可怕、難堪的霸淩。
霸淩者以霸淩為樂,他們享受這種作惡的過程,享受這種用暴力獲得的權力和快感。
他們,在不停地淩辱我,從肢體到心靈,四年級的我,體無完膚。
最後,故事是如何結束的呢?
有時候我會感慨,經歷過霸淩的我,又是如何可以活得還算健康,這是內心的心理抗壓力嗎,還是我個人只是剛好幸運。時間會抹平我們所經歷過的所有傷痛,然而回到當初,看著手足無措的自己,又得多心疼。
長達一年的霸淩從來沒有人發現,學校和家庭也從來沒有介入過干預,年幼的我也從來不知道應該如何尋找幫助,找老師、家長或者其他人,基本上是我從來沒想過的。我找過其他朋友,但是他們害怕霸淩者,我嘗試自己組建圈子,但是我從來都沒有離開過霸淩者的掌控。是的,我就好像是霸淩者的寵物一樣,她並不願意我有其他的圈子,我也嘗試融入霸淩者讓她喜歡上我,但是我需要出賣自己的堅持和原則。
最後一刻,“我”介入了。
在四年級最後一個學期結束,下學期開始之前,我和父母說:
“爸爸媽媽,讓我轉學吧。”
我用了一個很幼稚的理由,因為當年中學是分區的,派位是電腦隨機分配。在霸淩者所在的學校,會被電腦派到綜合素質比較差的學校裡,我告訴父母,我想考全市最好的中學,我想轉學到那個學區。
是的,我沒有勇氣說出自己被霸淩的事情,而是找了一個藉口。
這個理由正經得完全沒有一點不恰當,父母欣然答應,便火速幫我辦理。當時,因為醫學的幫忙,母親的身體狀況開始有很大的起色,父親的事業也穩定起步,我們搬了家,換了一個學區,母親說,“孩子,我已經康復了,讓我來好好照顧你。”
換了一個新學校,對我來說是一個“重生”,很陌生,但是也很害怕。所以當我第一天站在班級門口,我完全不敢進去,在樓梯旁邊的窗臺站了很久,我趴在窗臺,看著樓下,卻始終不敢回頭看我的新班級。
很害怕,但不知道可以怎麼辦。
可是我真的很幸運呢,那天有一個小女孩來接我進入課室,她笑著拍著我的肩膀,把無措的我拉進課室,鄭重地把我介紹給全班同學,告訴我,“大家,這是我們班的新同學哦!我們的好朋友又多了一個!”
然後全部的女孩子都笑了,不停地挪自己的位置招呼我,“坐我這裡,坐我這裡,我叫XX,很高興認識你啊。”
…………
如果有所謂的創傷後遺症,我的治癒是從五年級開始的。我進入了一個很溫暖的大集體,然後從那一刻開始,我再也沒有遇到霸淩。
友情,永遠都是霸淩最強大的敵人。擁有友情,懂得如何友善對待他人,感受如何被人真心和真切的呵護,是霸淩最強大的治癒武器。
作為一個被霸淩長大的孩子,長達十幾年的人生治癒過程,是怎麼樣過來的呢?
擁有這樣子的霸淩的經歷,成為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往事。學會如何和過去的悲傷和難事共處,並學會治癒和面對難事,也許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事情。
這個經歷多多少少影響到了我的個性。我學會了察言觀色,我會對互動、交流和情緒上的細枝末節比較敏感,因為這基本構成了我的本能應激反應。我也學會了去時刻保持反思,我學習客觀看待過去,優秀或者不優秀,並不是原罪。在被霸淩這件事情上,我們並不需要對此負責,犯錯者不是我們。
這個經歷多多少少讓我看到了原則和反抗的自我價值。我始終無法想像要是在當年,在沒有人説明的情況下,我如果沒有自己的堅持,沒有下定決心介入,現在的我,也許就再也不是現在的我了。所以我會感激“直覺”,對於原則的堅持和底線的不妥協,至少在最後一刻,救了我。我也學會挖掘自己的價值,積極去看待自己的優點和自尊,並且肯定個性中珍貴的部分。
這個經歷多多少少讓我看到了團隊、學校和社會的局限和作用。我在香港做社工的領域,主要是關注情緒,我學會用團隊療法、個案諮詢,包括社區運動,來達到整個集體的“賦權”,真正地為每個人提供治癒力。信任的人所帶來的支持和幫助是非常治癒的,真正的大集體,是最好的治癒源泉。
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清楚自己的能力,收穫了真正的友情和尊重,在不停建構更多的自我認同感和價值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地走出來,從這個童年的陰影裡走出來。
最後霸淩的孩子們,又是一個如何的成長故事呢?
我轉學後就再也沒有和他們見面,十年後在居然偶遇了。我帶著表弟去新華書店旁邊的麥當勞買霜淇淋。霸淩者圈子的其中一個人竟然認出了我,喊出了我的名字。
他們竟然認出了我,我覺得很尷尬,我想找個藉口離開。
他們很靦腆地一定要我留下來,並打電話讓其他人過來。原來霸淩者的圈子依舊還是霸淩者的圈子,他們從沒有瓦解過,從這個小學,到了那個中學和高中,然後高考失利,開始創業,始終還是在一起。
他們人齊了,他們竟然向我道歉。
“對不起,小時候這麼欺負你,當時我們都真的沒有當一回事。”
我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會道歉,這個結果是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的。不如相忘於江湖,但是其實對於霸淩者的他們來說,這些也並沒有被遺忘。
他們開始懺悔一般跟我講他們的童年故事。這是我們從來沒有交流過的故事和人生經歷。
他們反復地說,當時的壓力真的很大,父母覺得他們始終不夠優秀,而對比的我太優秀,無論在做什麼,老師的注意力始終都是在我身上。他們也享受霸淩我的過程,因為我手無足措、難堪的樣子讓他們感覺到有趣和獲得了假性自尊……
但他們也遭受了霸淩的代價。霸淩從我第一個開始,但卻並沒有隨著我的離開而終止,他們換了一個又一個霸淩對象,最後的代價是犧牲了學業,他們的學業越來越差,脾氣越來越暴躁,和父母的家庭關係也越來越不好。他們並沒有完全從霸淩中找到認同感,或者找到真實的友情和感情,他們在社會裡滾爬滾打了一圈,終於開始難過和懺悔。
“我用了整個人生,去替我當年的惡意來做補償。”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具體經歷了怎麼樣的波折,但他們哭得泣不成聲,在我面前手足無措。
那一刻,我才終於明白,原來霸淩行為對於霸淩者來說也是一種沉重的創傷。霸淩者也給自己設下了無限的圍牆和困境,懺悔和愧疚,是他們最大的枷鎖。
或許,最終都會在人生的坎坷中明白,無論生活境遇如何,都不應該成為霸淩的藉口。但卻並不是所有的霸淩者,都有機會可以去表達道歉。
看完近期網上傳播的帖子,說出我的故事,是一字一句一行淚的一篇剖心剖肺。
在學校和家庭都缺失的霸淩事件裡,給小孩子的衝擊,對小孩子以後生活的影響,是極其惡劣的,沒有安全感,不知道什麼才是朋友,害怕被人指手畫腳,會對整個環境產生害怕和逃避。
我是幸運的一個人,很幸運地一步一步地走了出來,並沒有留下陰影。但有很多的孩子,因為干預的太晚,對於之後生活的成長的負面影響並不可逆。
我在香港也跟進過很多相類似的案子。我們的原則核心有兩點:
1. 霸淩事件能否妥善處理和根治,關鍵在於學校。
雖然有三環,孩子、家長和學校都缺一不可。所以如果孩子真的遇到霸淩事件,能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學校。是的,很無奈,但學校才是最核心的要素。如果學校沒有規範的制度,從學校整個風氣到班級整個班級建設上都經營到位,警覺霸淩行為的不可被接受,提供足夠的援助給被霸淩的孩子,那麼霸淩事件基本上無法真正杜絕。
2.霸淩事件能否可以被知道,被霸淩者的父母很重要。
很多被霸淩的孩子並不敢主動和父母告之,因為霸淩是一個長期固定的相處模式,並且孩子們都會遇到威脅和新生恐懼。父母能否觀察到孩子的狀態,發現問題,看到孩子的主觀感受是相當關鍵的緩解。
在這兩環都能打通的情況,學校和家長可以通力合作,霸淩事件一般是可以從制度上得到緩解,通過教會孩子去修復傷口,包括堅持原則和反抗,孩子們也可以學會如何應對欺負。
在一個制度良善的學校,即便是班上有人際關係技巧較弱的孩子,也不見得一定會發生霸淩事件。
我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大家都很害怕霸淩者,因為她儼然把握了班裡的所有話語權,所以我和其他朋友的相處,是看著霸淩者的眼色來定相處程度的。霸淩者主動親近我了,大家就和我玩,霸淩者開始欺負我了,大家就遠離我。
我開始逐漸發現,我變得越來越不像我,變成一個越來越讓我厭惡的自己。
要融入到霸淩者的圈子,要先學會賄賂,我得先偷偷地把自己的壓歲錢從奶奶贈給我的小豬儲錢罐裡拿出來。錢越來越少,爺爺發現了,那天他來問我:“是學校裡要交什麼費麼,怎麼感覺壓歲錢都快沒了?”,那次對話我一輩子也忘記不了,我耷拉著點頭說,“是的,是的”。
要融入到霸淩者的圈子,要先學會跟隨,丟掉自己的主見,唯唯諾諾,唯霸淩者的話是真理,我開始晚出晚歸,因為我要幫霸淩者做完作業,替她籌備好明天上學的東西,我才能夠回家。
我從小都是一個乖巧、愛學習、全部人眼中可愛、聰明又優秀的孩子,但是我將自己珍惜的壓歲錢,將自己珍貴的品質,卻拿來作為賄賂的籌碼,換來別人假假真真的“接受”。
當我終於接受不了,放棄這種做法的時候,不出意外,我遭受到了更可怕、難堪的霸淩。
霸淩者以霸淩為樂,他們享受這種作惡的過程,享受這種用暴力獲得的權力和快感。
他們,在不停地淩辱我,從肢體到心靈,四年級的我,體無完膚。
最後,故事是如何結束的呢?
有時候我會感慨,經歷過霸淩的我,又是如何可以活得還算健康,這是內心的心理抗壓力嗎,還是我個人只是剛好幸運。時間會抹平我們所經歷過的所有傷痛,然而回到當初,看著手足無措的自己,又得多心疼。
長達一年的霸淩從來沒有人發現,學校和家庭也從來沒有介入過干預,年幼的我也從來不知道應該如何尋找幫助,找老師、家長或者其他人,基本上是我從來沒想過的。我找過其他朋友,但是他們害怕霸淩者,我嘗試自己組建圈子,但是我從來都沒有離開過霸淩者的掌控。是的,我就好像是霸淩者的寵物一樣,她並不願意我有其他的圈子,我也嘗試融入霸淩者讓她喜歡上我,但是我需要出賣自己的堅持和原則。
最後一刻,“我”介入了。
在四年級最後一個學期結束,下學期開始之前,我和父母說:
“爸爸媽媽,讓我轉學吧。”
我用了一個很幼稚的理由,因為當年中學是分區的,派位是電腦隨機分配。在霸淩者所在的學校,會被電腦派到綜合素質比較差的學校裡,我告訴父母,我想考全市最好的中學,我想轉學到那個學區。
是的,我沒有勇氣說出自己被霸淩的事情,而是找了一個藉口。
這個理由正經得完全沒有一點不恰當,父母欣然答應,便火速幫我辦理。當時,因為醫學的幫忙,母親的身體狀況開始有很大的起色,父親的事業也穩定起步,我們搬了家,換了一個學區,母親說,“孩子,我已經康復了,讓我來好好照顧你。”
換了一個新學校,對我來說是一個“重生”,很陌生,但是也很害怕。所以當我第一天站在班級門口,我完全不敢進去,在樓梯旁邊的窗臺站了很久,我趴在窗臺,看著樓下,卻始終不敢回頭看我的新班級。
很害怕,但不知道可以怎麼辦。
可是我真的很幸運呢,那天有一個小女孩來接我進入課室,她笑著拍著我的肩膀,把無措的我拉進課室,鄭重地把我介紹給全班同學,告訴我,“大家,這是我們班的新同學哦!我們的好朋友又多了一個!”
然後全部的女孩子都笑了,不停地挪自己的位置招呼我,“坐我這裡,坐我這裡,我叫XX,很高興認識你啊。”
…………
如果有所謂的創傷後遺症,我的治癒是從五年級開始的。我進入了一個很溫暖的大集體,然後從那一刻開始,我再也沒有遇到霸淩。
友情,永遠都是霸淩最強大的敵人。擁有友情,懂得如何友善對待他人,感受如何被人真心和真切的呵護,是霸淩最強大的治癒武器。
作為一個被霸淩長大的孩子,長達十幾年的人生治癒過程,是怎麼樣過來的呢?
擁有這樣子的霸淩的經歷,成為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往事。學會如何和過去的悲傷和難事共處,並學會治癒和面對難事,也許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事情。
這個經歷多多少少影響到了我的個性。我學會了察言觀色,我會對互動、交流和情緒上的細枝末節比較敏感,因為這基本構成了我的本能應激反應。我也學會了去時刻保持反思,我學習客觀看待過去,優秀或者不優秀,並不是原罪。在被霸淩這件事情上,我們並不需要對此負責,犯錯者不是我們。
這個經歷多多少少讓我看到了原則和反抗的自我價值。我始終無法想像要是在當年,在沒有人説明的情況下,我如果沒有自己的堅持,沒有下定決心介入,現在的我,也許就再也不是現在的我了。所以我會感激“直覺”,對於原則的堅持和底線的不妥協,至少在最後一刻,救了我。我也學會挖掘自己的價值,積極去看待自己的優點和自尊,並且肯定個性中珍貴的部分。
這個經歷多多少少讓我看到了團隊、學校和社會的局限和作用。我在香港做社工的領域,主要是關注情緒,我學會用團隊療法、個案諮詢,包括社區運動,來達到整個集體的“賦權”,真正地為每個人提供治癒力。信任的人所帶來的支持和幫助是非常治癒的,真正的大集體,是最好的治癒源泉。
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清楚自己的能力,收穫了真正的友情和尊重,在不停建構更多的自我認同感和價值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地走出來,從這個童年的陰影裡走出來。
最後霸淩的孩子們,又是一個如何的成長故事呢?
我轉學後就再也沒有和他們見面,十年後在居然偶遇了。我帶著表弟去新華書店旁邊的麥當勞買霜淇淋。霸淩者圈子的其中一個人竟然認出了我,喊出了我的名字。
他們竟然認出了我,我覺得很尷尬,我想找個藉口離開。
他們很靦腆地一定要我留下來,並打電話讓其他人過來。原來霸淩者的圈子依舊還是霸淩者的圈子,他們從沒有瓦解過,從這個小學,到了那個中學和高中,然後高考失利,開始創業,始終還是在一起。
他們人齊了,他們竟然向我道歉。
“對不起,小時候這麼欺負你,當時我們都真的沒有當一回事。”
我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會道歉,這個結果是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的。不如相忘於江湖,但是其實對於霸淩者的他們來說,這些也並沒有被遺忘。
他們開始懺悔一般跟我講他們的童年故事。這是我們從來沒有交流過的故事和人生經歷。
他們反復地說,當時的壓力真的很大,父母覺得他們始終不夠優秀,而對比的我太優秀,無論在做什麼,老師的注意力始終都是在我身上。他們也享受霸淩我的過程,因為我手無足措、難堪的樣子讓他們感覺到有趣和獲得了假性自尊……
但他們也遭受了霸淩的代價。霸淩從我第一個開始,但卻並沒有隨著我的離開而終止,他們換了一個又一個霸淩對象,最後的代價是犧牲了學業,他們的學業越來越差,脾氣越來越暴躁,和父母的家庭關係也越來越不好。他們並沒有完全從霸淩中找到認同感,或者找到真實的友情和感情,他們在社會裡滾爬滾打了一圈,終於開始難過和懺悔。
“我用了整個人生,去替我當年的惡意來做補償。”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具體經歷了怎麼樣的波折,但他們哭得泣不成聲,在我面前手足無措。
那一刻,我才終於明白,原來霸淩行為對於霸淩者來說也是一種沉重的創傷。霸淩者也給自己設下了無限的圍牆和困境,懺悔和愧疚,是他們最大的枷鎖。
或許,最終都會在人生的坎坷中明白,無論生活境遇如何,都不應該成為霸淩的藉口。但卻並不是所有的霸淩者,都有機會可以去表達道歉。
看完近期網上傳播的帖子,說出我的故事,是一字一句一行淚的一篇剖心剖肺。
在學校和家庭都缺失的霸淩事件裡,給小孩子的衝擊,對小孩子以後生活的影響,是極其惡劣的,沒有安全感,不知道什麼才是朋友,害怕被人指手畫腳,會對整個環境產生害怕和逃避。
我是幸運的一個人,很幸運地一步一步地走了出來,並沒有留下陰影。但有很多的孩子,因為干預的太晚,對於之後生活的成長的負面影響並不可逆。
我在香港也跟進過很多相類似的案子。我們的原則核心有兩點:
1. 霸淩事件能否妥善處理和根治,關鍵在於學校。
雖然有三環,孩子、家長和學校都缺一不可。所以如果孩子真的遇到霸淩事件,能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學校。是的,很無奈,但學校才是最核心的要素。如果學校沒有規範的制度,從學校整個風氣到班級整個班級建設上都經營到位,警覺霸淩行為的不可被接受,提供足夠的援助給被霸淩的孩子,那麼霸淩事件基本上無法真正杜絕。
2.霸淩事件能否可以被知道,被霸淩者的父母很重要。
很多被霸淩的孩子並不敢主動和父母告之,因為霸淩是一個長期固定的相處模式,並且孩子們都會遇到威脅和新生恐懼。父母能否觀察到孩子的狀態,發現問題,看到孩子的主觀感受是相當關鍵的緩解。
在這兩環都能打通的情況,學校和家長可以通力合作,霸淩事件一般是可以從制度上得到緩解,通過教會孩子去修復傷口,包括堅持原則和反抗,孩子們也可以學會如何應對欺負。
在一個制度良善的學校,即便是班上有人際關係技巧較弱的孩子,也不見得一定會發生霸淩事件。